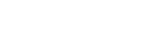如果说记忆是无花的蔷薇,永远不会败落,那么毫无疑问《童年往事》就是侯孝贤导演生命中的这株蔷薇。很难想象一个当时只有三十几岁的导演能拍出一部如此丰富的电影,这种丰富不仅仅指向电影故事层面、视听层面,更直接指向影片的情感层面。艺考传媒培训一致认为这是一部让人忍不住要感慨、要怀旧的影片。
影片是在一段不疾不徐的画外音中开始的,伴随着成年阿孝的内心独白,一股回忆的气息也迎面扑来。“这部电影,是我童年时期的一些记忆,尤其是对父亲的印象……”。与声音同步,画面也开始介入,先是高雄县宿舍的门牌、空无一人的屋子、摆放着台灯的写字台和空荡的藤椅,然后镜头再次切换,出现父亲一边吃东西一边看书的情景,小孩子们嬉笑打闹的场景,母亲和姐姐做饭的场景。开场四分钟,导演的镜头始终默默注视着这个看似平凡的家庭,久久不愿离去。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净土,譬如童年。侯孝贤也是一样。在这部自传体电影作品中,导演将主人公阿孝设置成一个再普通不过台湾少年——他有时调皮捣蛋,会让扎破老师的车胎,会偷剪电工的电线,也会偷母亲的钱;他有时顽劣不堪,他混帮派,看禁书,打撞球,他砸碎别人玻璃,泡马子,找妓女,他因副总统陈诚入殓与老兵发生冲突;但他到底还是善良可爱的,他因为没有照顾好祖母而自责,他会为弟弟妹妹做好便当,他因目睹别人境遇不如自己主动提出不用对方还钱。《童年往事》描绘了主人公阿孝在小城凤山从读小学直到当兵以前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精彩的呈现了一个少年由青涩到成熟的蜕变,并进而折射出近几十年来台湾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迁。
《童年往事》是导演对其个人记忆与民族记忆、时代记忆的完美整合。在阿孝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太多侯孝贤的影子,也读解到那些属于所谓“迁台第三代”共同的欢愉和悲伤。日式民居承载着台湾抹不去的历史,撞球厅是一个少年对叛逆青春的最鲜明记忆,停不下来的陀螺就像是关于过去岁月那永难褪去的相思,喋喋不休的老式收音机则是那个时代台湾与大陆连接的唯一纽带。值得一提的是,“迁台第三代”的共同记忆不仅来自于由日式民居、老式收音机等时代符号所引发的单纯集体怀旧,更源于深植于父辈、祖辈内心深处复杂的“历史情结”。
在祖母心中,永远有一条通往大陆的路。在她的逻辑里,只需这样沿着大路一直走,翻过大坝,就能走到梅江桥。但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她带领一脸懵懂的孙子左冲右撞,终于还是没有找到那条路。穷途末路似阮籍,本是该大哭一场的。但祖母的脸上竟然没有忧伤,她只是若无其事和连什么是“进祠堂”都不懂的孙儿一起做着“抛芭拉”的游戏,笑意盎然。
祖母是《童年往事》中最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她所代表的是那个“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不管外部世界如何变幻,祖母的精神世界始终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与之
相比,父亲、母亲的世界则是有缺口的,这也正是父亲、母亲会因为大陆的变化而忧伤祖母却不会的原因。祖母始终是高兴的,在她为自己搭建的体系里,从来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政权的更迭、外部世界的变迁从不对祖母的思想构成威胁。在祖母的世界里,台湾就是大陆,从家里出门走上几步就是梅江桥。也或许其实她心里清楚台湾不是大陆,她只是不忍心让自己去面对这个悲情的现实,于是宁愿躲进一个叫做“回家”的游戏里,一个人玩得不亦乐乎。而任何游戏都会上瘾的,这样以后,“回家”之于祖母,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行为,它成了一种习惯,成了她在这个冰冷小岛活下去的唯一寄托。
“迁台第二代”的代表是父亲和母亲。电影中的父亲是不多话的。影片中只有两次对准父亲脸部的特写镜头,并让父亲开口说话。一次是收音机里播放妈祖海峡空战的捷报时,父亲一边吃甘蔗一边缓缓开口,讲起自己在广东中山大学念书时旧日好友的故事。还有一次是读大陆亲人写来的信时,与母亲说起大陆大炼钢铁的惨况,唏嘘不已。与祖母类似,父亲的精神世界也是封闭的,但这种封闭有一个缺口,缺口通过收音机的电波指向大陆。对他来说,台湾只是一个过渡,大陆才是家园。这也正是他买竹制家具并且迟迟不肯给母亲买缝纫机的原因。但理想主义的光芒终将退去,在面目可怖的现实面前,父亲陷入了深深的抑郁——这是属于那个时代迁台知识分子们共同的抑郁。当一直坚守的理想一步步被现实抽空,当返乡梦伴随着对岸亲人的噩耗被一点一点吞噬殆尽,他不可能不绝望。哀莫大于心死。那么等待父亲的,似乎也只剩下死亡这么一条路。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死亡不仅是肉体层面的陨灭,更是“迁台第二代”精神层面上“中国梦”的破灭。
虽然电影中父亲只与阿孝有过两次简单的对话,但是父亲的溘然离世,对于阿孝依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导演没有安排阿孝扑倒在父亲遗体上声泪俱下的煽情场面,他只是让阿孝远远地看着父亲,看父亲吐在书卷上的血迹,看医生来为父亲问诊,看母亲扑在父亲遗体上嚎啕大哭。节制的哀伤不仅没有削弱电影的悲剧气氛,反而营造了一种疏离的哀伤感,简单质朴却又感人至深。
母亲是父性式微图景下对父权的一种补充。对于阿孝来讲,父亲在他的生活中其实是缺席的。缺席并非不存在,只是对于阿孝的成长,父亲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前文中已提到父亲与阿孝的交流只有很少的两次:一次是父亲递给阿孝新撕下来的邮票,还有一次是阿孝考取省立凤中时父亲对他的鼓励。如此贫瘠的关爱,即使是在母亲追赶因为偷了五块钱而挨打的阿孝时,父亲也是不置一词。与之相对应,在生活中母亲承担起了父亲的角色,这种作用在父亲去世后体现的更为明显。但是不久母亲也得了喉癌。
如果说父亲的去世对于童年时代的阿孝还只是一个模糊的记忆,那么母亲的去世则为阿孝的人生烙下永难抹去的印记。也是这个原因,在母亲病重的那一夜,阿孝没有参加帮派之间的打斗,他选择了守在母亲身边。但死亡终究是不可逆的,该来的还是逃不过,母亲离开了阿孝。依旧是再节制不过的表述方式,简单质朴的葬礼,众人齐唱赞美诗。与父亲葬礼不同的是,在一片静默中,阿孝幽幽的哭了。这是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哭泣。在这里,阿孝流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眼泪,更是“迁台第三代”共同的泪水。母亲的死去,让阿孝成为彻底的“浮萍”,“无根一代”从此也成为“迁台第三代”永难逃离的宿命。
固定机位长镜头、景深镜头、远景、空镜头一直以来都是侯孝贤电影的特殊标签,深深印刻在每部侯孝贤执导的影片里。而《童年往事》作为其代表作之一,更是将他的美学品味显露无疑。不同于他后期作品如《最好的时光》、《海上花》中对镜头时长、场面调度的精准掌握,《童年往事》中一些漫不经心、突然无规律的跳切和较为灵活的运镜方式为这部自传式的电影添加了许多时代的韵味。作为电影的两个主场景:阿孝的家和人群聚集的十字路口承载着侯孝贤对自己真切的生命体感和台湾历史的沧桑巨变。在对阿孝的家更具体的说是阿孝父亲居住场景的展现中,镜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了父母亲生活环境的最大的完整性。与小津安二郎相似,导演用景深镜头和长镜头把握住了整个房子的通透感和真实感;而不同于小津安二郎惯用的中景、中近景来表现对剧中人物关切的方式,侯孝贤让镜头退出屋子,甚至在看似通透的空间环境里用占很大面积的门作为前景的遮幅,侯孝贤导演采用客观的视角从远处静静注视他电影中的人物,使平凡的家庭生活演变也具有了史诗般的格局。而用远景横移的长镜头记录下的十字路口的人生百态,也像画幅般一一展现。
电影中的生与死、成长与离去,流露着侯孝贤独有的生命体验。在电影的表情达意方面,配乐起到了很大作用。不同于侯孝贤后期作品中对音乐的谨慎使用,《童年往事》可以说是一部太过温情的影片,影片充斥的不是理性的思辨而是满满的人文关怀,温情柔长的旋律时时萦绕在观众耳畔。尤其伴随着祖母的出场、祖母与阿孝采芭拉以及祖母的离世,这种老与小、生与死的对照,更是让人充满惆怅的同时又无限感怀。
电影的英文名字是“TheTimetoLiveandtheTimetoDie”,为生而死,向死而生。也或许只有经历了至亲的相继离世,懵懂的孩童阿孝才能真正长大。无法言说悲恸体验,就这样悄然化作成长的肥料。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城南旧事》中小英子的那句话,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一代的成长总是要以上一代的凋零为代价,只是随着这份沉重地成长,一个时代也该谢幕了。长歌当哭,却哭不出。那就留一份淡然的心境来静看这世事更迭吧,像杨慎那样,在洞明一切之后,只需“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