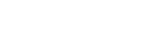1994年戛纳电影节上,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凭借《低俗小说》打败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红》摘得金棕榈奖,引发影坛热议,所以本期小编带来了对这位导演电影风格的解读,帮助南京编导艺考培训和广大编导艺考生拓展知识面。
学术界非常重视昆汀导演影片中的后现代主义元素,积极开展了大量社会学、传播学等方向的研究;而同时昆汀导演因其独特的风格被影迷逐渐捧为大师,对其赞誉有加并争相效仿。本文尝试对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电影作品及其电影观念开展批评,旨在从电影创作本身而非社会文化现象分析的角度,审视昆汀作为电影导演的艺术成就,试图对当前的昆汀电影研究现状提出一些建议、提供更丰富的思路。
毋庸置疑,被誉为“鬼才导演”的昆汀·塔伦蒂诺,在电影手法、美学理念、叙事策略乃至音效配乐等方面对电影语言的丰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极大地拓展了电影表现力并对同期的电影创作投射了巨大的影响力。此外,本身身为职业编剧的昆汀,始终坚持指导自己创作的剧本,高产的电影(影视)文学创作展现其编剧才华的同时,在编导合一中诠释了作为独立电影人的强大行动力和作者原创性。从昆汀进入评论界视野之始,其游离与主流电影文化之外、不惮于拥抱通俗文化的姿态就激起了业界人士及电影观众的热烈讨论。尽管作为新兴的流派免不了面临不理解和不接受,但随着人们对当代文化趋势愈来愈深入的把握和确证,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当代文化认同的迫切需要,昆汀及其电影风格受到持续的大量的关注,在其影迷范围内受尊崇和追捧亦不足为奇。
以上,试概述近二十年来对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接受情况。诚然,昆汀的电影已然成为影史一只不容忽视的力量,但本文拟从自我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三个方面入手,探究“昆汀热”背后可能存在的缺陷或隐忧,如若给予读者诸公些许启发则不胜荣幸。
在具体展开论述之前,笔者希望阐明这一批评的立场:事实上昆汀受到的大部分批评是从社会责任感或严肃性等角度考虑的,未免流于保守。本文希望摈弃老生常谈的陈词滥调,更多地从艺术家本体出发进行批评,由此将批评的主观局限性从一种他者眼光的评判转移到创作者角度的自省。
一、自我认同:昆汀的“招牌”和“挡箭牌”——游戏有无界限?
正如纷至沓来的评论研究所界定的,昆汀的电影有着显著的后现代主义风格。《低俗小说》可以作为昆汀对后现代娱乐性、游戏性精神阐释的最具代表性作品,糅合其他众多影片和文学作品的桥段和隐喻以及碎片化的美国社会文化于一身,将暴力、性、政治、历史都转化成玩笑,甚至有意让观众意识到:观看影片只是在参与一个游戏而已。就像影片中文森特在谈论关于米娅的传言时所说:“这些都不是事实,只是我的道听途说”、“让我们进入角色吧”——一切都不必当真,观众和剧中人所作的都只是进入角色完成这个叙事游戏。
“游戏”一词,不啻为昆汀的自我标榜,一以贯之。就风格而言,游戏化的视听语言与叙事方法给他的作品打上了显著的“昆汀式电影”的烙印,彰显出挑战传统、玩世不恭的气质,无疑是昆汀得以积累人气的重要因素。后现代社会一切艺术都渗透资本和商品的逻辑,成为大众消遣的工具。迈克·费瑟斯通对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特征作过这样的概括:“在艺术中,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关键特征便是: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层次分明的差异消弥了;人们沉溺于折衷主义与符码混合之繁杂风格之中;赝品、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反讽、戏谑充斥于市,对文化表面的‘无深度’感到欢欣鼓舞。”
当其游戏化的风格深入人心之后,俨然成为昆汀的一大招牌,这本身是非常成功的策略,它迅速建立起观众群,并有力撼动了传统的古板的强调逻辑的电影样式。然而,电影水平高低很重要的一点便在于如何运用视听语言调动观众感受,这也是电影生命力所在。因此,尽管昆汀戏谑的调侃埋藏着许多智慧,导演本人也意识到,迈向电影大师不能只依靠“小机灵”,实打实地训练视听语言的基本功必不可少。例如,《落水狗》开场的餐馆对话戏,“昆汀影迷”或许能注意到其实这是“反好莱坞的拍法”——谁说话偏不给谁镜头。加上这一层信息的话,这场戏就变成了独立电影打破好莱坞电影“僵化手法”的尝试。但如若没有这层信息,则只看到一场耍嘴皮子的戏。在《无耻混蛋》之前,昆汀其实都没解决这个问题,《落水狗》到《低俗小说》再到《杀死比尔》,可以发现昆汀一直在做加法,一直在往电影里塞各种“点子”,直到《金刚不坏》失败,他才沉下心来做减法,练硬功。
“游戏”在成为其风格特色的同时,俨然也成了昆汀反击批评的“挡箭牌”,而这对于导演本人的自我突破和发展是不利的,需警惕被“游戏”的思维所麻痹从而为技艺上的瑕疵开脱。《无耻混蛋》可以看作一个分水岭,至此昆汀才真正开始完全用视听语言而不是台词来讲故事。在这部影片中,昆汀较好解决了此前对话场面拖沓、视听语言稚嫩的问题,同时其代表性的“致敬老片”部分也并没有损失完整性,让观众也能感受到这种效果。(熟悉意大利西部片的观众能够辨识出二者相似的视听节奏。)《被解救的姜戈》同样走“回归正常道路”的叙事模式,一五一十地讲故事的基础上发挥才华。但遗憾的是,这种回归显露出昆汀作为编剧的一大硬伤:此前的成功是基于他创新型的非线性叙事、章节式回环等才华横溢的尝试,却掩盖了讲好一个严肃完整的、经得住推敲的故事的能力不足。同时,由于失去了诸如《低俗小说》复杂结构所能带来的掩护和分忧,昆汀的《无耻混蛋》与《被解救的姜戈》在收尾上略显尴尬。笔者所言之“挡箭牌”便是如此,虽然有意认真讲好一个故事(如设计精巧的二战谍战主题的《无耻混蛋》),然而所有因编剧能力不足或是其他因素导致的瑕疵都有了“游戏”风格的庇护,而变得可以被原谅。以至于昆汀究竟想借此生发思考未果,还是纯粹借用一个背景把玩已有的那一套技巧,我们很难分清。倘若《无耻混蛋》结局的颠覆历史可以被当作是彻头彻尾的讽刺和娱乐,《被解救的姜戈》则陷入了俗套的泥淖,以至于铺垫的戏剧能量并未燃烧殆尽,可供深挖的哲思功亏一篑。本片敢于深抵人性、超越“政治正确”地将种族问题以冷静而睿智的方式解读:抛弃纯粹的怜悯,赋予奴隶制背景下的非裔奴隶以真正的人性——有善亦有恶,有爱亦有自私,甚至振聋发聩地触及人的奴性——这种思考是难能可贵的。私以为,若将故事终止于坎迪别墅里的枪战,以悲剧告终,其思想性将提升一个台阶。无奈影片以最简单的复仇收尾,似有迎合观众的嫌疑。唯一可以解释的,恐怕是来自市场和舆论的压力。
昆汀电影剧情简单、叙事拖沓的问题确实被人诟病,有人一半批评一半辩护地指出,其影片亮点不在于剧情,而是过程,换言之可谓形式大于内容。由于昆汀的电影形式大于内容,在对昆汀的态度上,许多年轻的电影从事者容易进入一种盲目崇拜的境地。他们更多崇拜昆汀本人,而不是他的电影,乃至于有可能出现一味模仿形式而忽略了内容的境地。因此,笔者抛出“游戏有无界限”的诘问,希望昆汀“游戏”的风格与艺术水准间的博弈可以被重视。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衷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变化的某些方面”。昆汀自觉或不自觉地扛起了后现代主义电影的大旗,我们所做的不应只是趋之若鹜般的学习研究,更不能刻意模仿。
二、价值认同:模糊的美学追求与暧昧的道德立场——当电影成为目的本身
除去各类元素符号化的拼贴外,昆汀的每一部影片都会夹带大量的“迷影私货”,即通过各种经典老片桥段的戏仿来致敬前辈,甚至不惜拖慢整个电影的情绪节奏,而且“抄袭”也是他学习拍电影的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言,拍《杀死比尔》就是一个看老片(主要是香港武打片和日本刀剑片)学习如何拍动作片的过程。大量的戏仿是昆汀电影的另一大特色,将自己的作品拍成了一本活的电影史教科书。但这些“迷影私活”显然不适用于大多数人,有观众表示,影片中大量的“用典”对于非电影发烧友而言,很难发现导演设计的重重机关,有时还会影响情节的理解。对此,昆汀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有很多人谈到我看了太多的电影。哪有一种艺术会把成为专家当作坏事呢? 如果我是一位诗人,难道我会因为太了解萨芙或亚里士多德而被批评吗?” 作为“致敬”的“抄袭”本无可厚非,然而一旦沉迷其中,止于戏仿而鲜有创新,疏于打造属于自己的系统化的艺术构思,则显得不够专业——昆汀本人非科班出生,凭借对电影的热爱修得对影史的熟稔,本身缺乏理论学习——由着性子无止境的戏仿表现得更像是电影发烧友,而非专业的从业者,恐怕应当做一定的取舍。唯有属于自己的经典桥段才能留名影史,如《落水狗》中金先生割耳朵前的舞蹈,又如《低俗小说》里文森特和米娅的扭腰舞。
后现代派对于过去的重述之所以具有特色,就是因为这种重述与前代文本有一种说不清的矛盾关系,一方面意识到某些文本激发想象力的力量,但同时又意识到这些文本的意识心态或风格上的局限性(模棱两可的戏仿现象)。我们从昆汀略显混乱的拼贴重组当中,看到的不仅仅是后现代的表征,还有导演作为自觉的审美个体有些模糊的美学追求。当然,正如上一个问题所谈到的,“游戏化”等后现代的特征随时可以成为“挡箭牌”,目的性可以是不存在的,行为的目的可以是行为本身——当拍电影成为目的本身:为创意与才华的施展找到载体——便无法苛责,否则被倒打一耙为来自精英传统的非难。
论及昆汀电影中最不可或缺的因素,恐怕是暴力。昆汀的电影里不仅上演着影像暴力,也充斥着喋喋不休的语言暴力。(语言暴力和影像暴力是并存的,两者巧妙地融合。)总结昆汀对于电影中大量直接的夸张的暴力展现的理解,须联系前文提及的“游戏化”倾向。昆汀的暴力是后现代语境下对暴力本身的意义解构,是对暴力一词能指和所指的剥离,即暴力即暴力本身,是“超脱的道德感”下的暴力游戏化和娱乐化。首先,是游戏式的暴力。昆汀有意使暴力场面变得荒谬滑稽,这种调侃似的表达极具黑色幽默的特色。昆汀瓦解了传统对于暴力的界定,更颠覆了暴力的实质,暴力不仅仅是血腥和痛苦,在其影片中只是一种游戏。暴力在戏谑的氛围中已然逝去了血腥残酷的原色,只留下了部分戏剧冲突,成为闹剧,目的是提高影片的观赏感。其次,是道德感的缺席,严格来说是意义的缺席。昆汀电影中的暴力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并且被广泛应用与研究,就是在于它放弃了对暴力“合理化”的企图,弱化甚至取消了观影者对“暴力是否合法化”的追问,目的是使得暴力的攻击性得以软化,暴力变得容易被接受,仅保留风格化暴力带来的快感。例如,昆汀谈到《杀死比尔》中女主角在雪地与反派决战用日本刀削去其头皮的场景,说道:“这应该既是有趣的又是充满诗意的,还带着有一点点的庄严。当你看到她的头,这很滑稽。然后她的台词说,‘那真的是一把服部半藏锻造的剑’,这很有趣。但是,接下来的镜头并不好笑,当她栽倒在地,而背景乐响起梶芽衣子(歌手)所唱的关于复仇的歌。所以多种感觉混在一起:滑稽、庄严、唯美、恶心,同时发生。” “电影中的暴力可以很酷,”他说,“这只是另一种可使用的颜色。当Fred Astaire跳舞时,并不意味着什么。暴力是一样的,这并不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颜色。”他蔑视任何试图看到模拟暴力具有意义的人。他说:“吴宇森对于暴力有很深刻的见解。他这么做,是因为他对此得心应手。”他称赞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发条橙》,他说:“他对暴力的钟情不止一点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任何声称自己作品是纯粹审美的艺术家,要么是轻佻的,要么是精神错乱,要么是在说谎。有批评家指出:“他把痛苦变成了一个柔美的笑话。从《低俗小说》到《杀死比尔》,他鼓励观众对酷刑,残害和鸡奸报以大笑。在《无耻混蛋》中,一群卧底在德国的犹太人折磨和并割去纳粹的头皮,他使观众看着那些人活活被刀刻而呻吟着,并对此哈哈大笑。我不相信艺术作品应该是圣洁的。我不相信英雄应该是善良的,或者坏人应当有报应。艺术作品可以展现深刻的暴力和残酷的人,并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恶人可以是潇洒和成功的,也可能从不为他们的残酷付出代价。但是不应该告诉我们,人类的苦难本身就是微不足道的。 永远不应当把痛苦变成笑料。”暴力对电影具有特别的力量,正是因为它不由自主地激活了我们的同情心。这是一种奇妙的反射,我们想象自己陷入痛苦(内模仿)。这是我们文明最本能的本能:对痛苦的陌生人产生同情。任何否认这种意义,即基于颠覆它的艺术作品,最终都会被玷污。这并不是说让人暴力。但它确实让观众在道德上被腐蚀了哪怕一毫米——在昆汀的后期电影,留下的只是一点点萎缩的道德力量。昆汀认为,暴力场景并不会教导少年尝试暴力,只会让他们爱上暴力风格的电影[3],恐怕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语言暴力亦如是,我们可以将语言暴力理解为以语言霸权的形式,通过不讲逻辑、不合规范的语言的大量使用,吸引观众的注意,孤立和剥夺他人的某种权利,造成伤害的实质。昆汀反复强调,其电影中的暴力是娱乐化的消解了意义的打造风格的手段,却对自己的道德立场避而不谈。在这个时代,强求艺术家遵守道德早已过时,但模棱两可的道德立场可谓某种责任逃避。
电影为荧幕构成一个严丝合缝的模拟领域,妨碍了我们对于“真实现实”的获得。当人们在社会新闻里听闻有关暴力的报道,观影经验或将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暴力的认识和判断,因为相似的情节已然在荧幕上被模拟过了,尤其对于青少年而言不利于建立起对暴力的正确认识。
三、文化认同:亚文化背后的自信与自觉——“通俗文化”是伪命题
后现代主义标志着一种与现代主义精英意识的彻底决裂,反对一切权势话语、中心与等级,以一种接纳一切文化的平民姿态,解构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精英立场。后现代主义艺术形式最常见的策略,是动摇纯艺术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途径就是通过借助大众传播的符号。后现代电影电演同样以娱乐性和消费性作为支点,创作出具有游戏特征的文本达到自我与大众的狂欢境界。这种后现代电影既是生产又是游戏,让观众看到影像的狂欢,在对传统现行叙事结构的颠覆中张扬作者的叙述快感,并让观众享受到参与叙事游戏的愉悦体验。昆汀的影片里没有权威叙事与精英意识,上帝的视点屡次被戏耍和嘲弄,充斥着暴力与詈语,处处都在彰显他反文人式高雅口味的创作倾向,用低俗文化去冲破精英文化建立的藩篱。
有一些学者就此给昆汀的电影打上“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的标签,私以为是草率而不负责任的。精英文化的对立面不是通俗文化——通俗文化或为伪命题,因为它很难被当作一个整一的文化群体——与精英文化的高度理论化体系化不同的是,“通俗文化”正因为其群口难调而不成体系,松散而复杂多样。后现代主义是对于现代派自我封闭的反动,确保了为艺术家提供观众和影响范围,但这些观众在日趋减少,影响范围也日趋缩小。与其认为昆汀代表了“通俗文化”对传统电影工业的挑战,不如说昆汀始终代表着一种亚文化群体,正如电影领域流行的B级片或Cult Movies,其本质是有着剑走偏锋的艺术追求、游离在主流之外的边缘亚文化群体。尽管由于资本的介入、名气的飙升,这种亚文化的群体越来越大,终究不能简单地和“通俗文化”亦或是“大众文化”画上等号。
回到对导演本身的批评上来,则由此作出假设:怪诞的风格化的电影语言、犬儒的世界观、为反叛而反叛和为游戏而游戏的思想,是否均来自于新兴的亚文化群体的自我认同和自我确证。这一论断并非站在主流文化的角度倨傲地审视这一文化现象,而是试图看到其背后地不自信与不自觉。例如,导演处女作《落水狗》,是詈语密度最高的作品:真正的语言暴力不是通过满嘴的脏话达到的,而是在适当的时候以最恶毒的方式挑衅和谩骂——这一点在《被解救的姜戈》中得到较好的贯彻——之所以前期的詈语使用显得滑稽可笑,不仅仅是刻意的娱乐化消解,而是导演侧重于建立风格因而缺少自觉性。
而当风格建立后,在经历一系列同质化的尝试走向下坡路之后(《金刚不坏》取得失败,昆汀自己承认了这一点),导演不得不转型,于是回归到传统叙事,有了《无耻混蛋》等作品的尝试。从主观上分析,导演须保持自己的创作活力,维持既有风格;从客观上看,导演需要观众的支持、需要票房的保证——昆汀热爱电影事业,但前提是成功的市场反馈——他曾表态有退居职业编剧的考虑,唯有商业的成功是热情的助燃剂,支撑其奋战在一线,为影迷奉献新的佳作。
我们不能简单将电影分为“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如今的电影产业二者可以相容——真正对立的是“产业化”的电影与独立电影——不能单凭商业性与艺术性划分,更大的差异在于创作者的动机。从这个角度看,昆汀无疑是纯粹的影人,这是其人格魅力的根源。
【参考文献】
1.〔荷兰〕杜威·佛克马.走向后现代主义〔M〕.王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7.
2.〔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J〕.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
3.〔美〕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4.〔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M〕.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
5.〔美〕罗伯特·艾伦.重组话语频道: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二版).牟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
6.《低俗小说》与昆汀·塔伦蒂诺的后现代文化注解,杨慧颖,理论观察,2015
7.解析昆汀·塔伦蒂诺电影中的暴力,李琳,电影文学,2016
8.“电影顽童”的黑色游戏王国——昆汀·塔伦蒂诺电影研究,陈景丽,2008
9.为什么昆汀会被广泛地尊为大师? 知乎用户Martin的回答